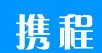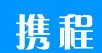������Ӱ|������
�������빬��һλ�����ʵ۵������ͼ
����������һ�������������ɽ���������һƬ���120��������˷��棬���ǽ�2000��ǰ�������ʵ۹��������빬�����ﲻ��Ѱ������Ѱ�����ֵĺ��ݱ�����������λ�������������ռ�������ȫ�����������۵ġ�����ǡ���
�������������������ȴ����Ƿ���ɭ�ϵ����ӣ�ӵ���и��Գ�Ĭ���ƾɵ����������ֱ������Ļ���ζ�����������ĵ������飬ׯ�϶�Ϸ���ţ����������¡¡�������硣��Ȼ��վʱ���ѵ�һ�죬�ܾ���ͷ�Ϸ���ǧ��ľ�����������������������ͷ����������У���Ȼ������һ�����ƣ��������ǻ����Ķ���������
��عż������������������ܹ�Ҳֻ���������������ߡ��������ıڹŶ����ˣ��������赭д�ر�Թ�Լ�û�ط����Ŵ�һ���������˼ɵ��ִ���������������������˼ɡ������ٹ������������ż���֮�������ڽ���֮�������һ�����������������˧����Ů�ڽ��ּ���æ�����ˮ�����������������������ġ���֪����ȡ���Ϊ+�����������ʿɿ����ź����յĹ����������Ღ�س�һ�ۡ���ά�ż���Ҳ�����Ĺ㲩��Ȥ֮һ������������ʷ�ľ���֮����ʱ��ı�ϣ�����������ʷ�ľ�������ʷ�Ľ����������������Զ�Ľ��������㵹��ʯǽ���ҵ�ˮȪ�ķ��١������������ʵۣ��������dz������ŵ���ѧ���������ĺ����������ƹܵ۹�����ϣ����˼���������Ҳ�����ˣ�ʫ�ˣ����к������ӣ������İ��ˣ�ŷ��֪ʶ���ӵij��Ρ�
��·��ʱ��
��������һ�λ��ᣬ�����������ȹ����죬����������á�...�ؼ��˽��е���������������������¼��������ء���ɪ�ɶ���
2000����������ϱڲ�ԫ��Ѱ��ˮȪ�ķ��١�����������ˮ�źٵ������������������������õ�����������������ֵĻʵ�����������������30�������Tiburtineɽ�£������������ɽ������õؽ�����ˮ��ǽ���ִ˲�ƣ�����ij̶ȿ����տ�������ũ����20��ʱ��Ӫ������������һ��120����Ļ���¼��������֮�������꣬�����Ǵ��������ı������ᡢ��˹����.�²���Ү�����ұ������οͣ���ֻʣ�������Ұ�������ο͵ķݶ��ˡ�հ��ƾ����������˼֮�࣬��Ī���Դ���������
һ���ǣ�����֮��������������·�����ϵ�����������������ӻ����ұ���˴���ʯ����Adriana���·���˽�ͷ���ţ�ֻҪ˵�������֣�һ·�������Բ�ͨ��Ц�����еľ�������Ӧָ���������ڿ���Tivoli�İ�ʿ�Ͼ�Ȼ˯���ˣ�����վ�³����DZ�����Ц�������̫̫�����ѵġ�ȥ�빬��С·Ҳ����Ԥ�����ǰ��������������ò���ݵ������ﴩ�У�ȫ�����ξ����ܱ߹��е������̲����ࡢ�ؽֽ���֮����·��һ��Ժ�ӣ�������һλ��̫�������������տ��µ���ڴֵ����������Ǻܺ�ˬ������һ��Լ1���صĴ��ɹ���
�����ţ��������µ�ɽ���һ·�Dz����ɰغ�����֦Ҷ����������֡�������ַ����ľưɺ�ͣ�������ǵ�1958�����ɪ�ɶ�������ƽ����Ϊ�����ƻ��˲�������(Le
Poecile)ͥԺ�ĸ߹�¼�֮���������Щ���ʵġ��������ֶδ���Ѹ������ޣ����������������������ŵľưɱ���˺���������Сչ���Һ�¶��Ұ��������ϲ�����ּȲ�����ͿĨ��ȥ�ı������������������²ι��ߵķ�����һ���������С��Ů��СèС����ϯ�ض������������·�������������͡������ڹ����˽�ʵ���Ȫ��ȡˮ��Ϣ�ĵ��ڣ�С�������Ѿ�С���������û��մ���ʰ�òͺ��������Żغ��ᣬȻ��ı������ظ��Ŵ��˽���Ѱ�����������������ò��������С��������������������ᷴ�ԣ���Ӧ������ϲ�������������Ĵ��졪������֧�ŵ�ʯǽ��Ȼ���й�������Ӵ��������¡���δ����֮�ˣ�����˫�ָ����ҵ���������
����������
����Է�����ӽ�������֮�ء������ķ������ڴ˰�Ӫ��կ��ͥԺ�ɴ���ʯӪ����������Ϊ��������������������ͤ������������������¼����
�չ���Ŀ���ھ��Է��֮���������������������Դ˹��ߵ������٣����ţ�����������������һ��������ʷ���Ӵ˿�ʼ���𡣻�Ѫ�ĵ��к����ӣ����������壬ϣ����ͷ�ԣ��Ļ���ҵ�������������������صĶ��������빬����һ���villa������һ���dzء������������Լ�ƫ�����ܾ�֮�ش�����˹����������������ġ�City/Villa����
��Բ120������빬��д�С���������ԡ�����糡����������������ͼ��ݡ�ҽԺ��ʳ�ã���Ϊ��������������ū���������ᣬ���ӵĹ�ˮ��ϵ�����������ͨ�����Լ�����Χǽ��Ѳ�߸��ڡ���֮�糡��Maritime
Theatre���Ǿ���İ�������ʽ�����Թ����˫������Ͳβ����������ϣ��������Ӱ�ӣ��������ľ��ɵ��ź�˽�˿ռ��������ȴ�Ƕ�����Canopus�������Ű������е����֣���������������˹��ʽ�Ļ��Ⱥ����Թ�ϣ����������������������ʯ��ʽ������Serapeum��������ǰ�����ϣ����ڤ����ʥţ�����л�ˮ��������������Է���϶����룬��ͨ��һ����ˮ���ܵ���ɵĸ���ϵͳ����Ӧ�����и������䡪���������������ó��Ĺ��̡����Ǿ�����35��ˮ�ޡ�30��������Ȫ��12��������Ȫ��10����ˮ�ء�6����ԡ����6��ˮ������
�����������������ǽ�������ż����һ��Ƭצ�Ĵ���ʯ�����ˣ�������Сԡ�ҵĵذ��ƽ�㳡��һ�ǣ����˾��ޡ�����Ϊ��ʯ���ͽ��Ŀ�����˼�����֮����Է�������������ƴ�����������Ե��к��ذ����ص�ʯ�ģ�������α��ʵ�һ��龫��ϸѡ�����仨ɫ���ӵ���������������ƫ���õ�������ϩ�����ש����ȷ���ò��䣬�����ڵ��ϣ��ٶ�ʮ�־��������ػع����أ���ʵ�ο�����ʹ���䲻�ٱ��о�ʱ��¥�����������Ĺ��ò��Ҳ���������ɽ���������Щ��ʴ�����¥̨ͤ���Ѿ����ɻ�Ϊ��������Ź����֮ɽ�͡���乩�ϵ��ˡ����ʵۼ����͡����ר�õĴ������û���������Ӵ��˵ĵ���ͨ·����ͨ�˴ū�����������ڴ��İ������д�����µ����¥�ù����䴫�����Ƽ��ȡ���С�糡�д��ھ�����̨��ֻ�л������ݣ��������������֦��ǽ�붴��������ͼ��ݡ����Ⱥ���������һ�ֻ��Ұ����ˮ��к�ء�û�п���˵����˭���ϵó��ǸɺԵ�˶��ˮ��ԭ������ض���Ӿ�أ���رߵĿ���˹�����ӵض��Ű���������ңң�ֳ���ɽ�������де�С��ɽͷ��ѩδ����
ˮ���ڣ��������������岼��ˮ�����ޣ����ȴֻ��ɳĮ�����¼�������Ȫ��һ����Canopus��һ���ڡ���֮�糡����һ���ڡ��������ա���������IJ��������е����ִ�������˹����棬��Щ�鸡�Ŀ������У����Ի�������ˮ�����Ƶ����硣����֮��ʹ���лķ��������壬Ψ���ɺ�֮ʹ���������ͻ���������Ҫ�ؽ��������ģ��ˮ���̣���ʹ���ù������ļ��ɣ�Ҳ���ʱ����֮���������ȹ�������ۣ���������һ�ֻ�����
���������ֹ۴��룬��ˮ����δ��ʧ��16���͵Ļ�Ҫ��˹����Tivoli����Ϊ�Լ��Ľ�������Villa
d��Este��ʱ�����Ľ���ʦ��������������������˺͵��ܣ�Ҳѧ���˹������Ը���ˮ���Ľ�������������ո���ʱ�ڰ��Ӷ�뷢�ֵġ����С�֮��Сԡ���ͻƽ�㳡�ǰ���������洦���ּ����˰���˽���ʦ����У��籴�����ᣨBernini���Ͳ������ᣨBorromini�����ڽ��ú��������ڲ�����Ӧ�������ַ�������Լ������˹�𡢸����ˡ����ء��ա��²���Ү��·��˹������Լ����M��Լ��ɭ���������빬���ִ����������Ӱ�챻�Ը�����ʽ���������������Ƶ��Ϸ�������ѧ��Լ��ɭ��Ƶ�Mummers��
Theatre���������顤��Ү����ɼ��������ģ�The Getty Center�����������ڿռ��������Ļ������ϣ������������������Ļ���Ӫ��ɽͷ�Թ������빬��һ���ִ��泯����м̡������������������ں��ϵ�ֱ�����������ݱ�ݣ�oval����Ҳ����¶������֮�糡��������������λøС�
��������С˵�еĹ��������ԣ�������ijЩ����������������������Է�����������֮�¶���������ѿ����
���ߡ�����
�����������������ˣ���ȫ�����ɹۿ����ĸ���£����������Ⱥӡ����������Ժ�������䣬�ѵ�����һ�����������ϣ�����ְλ�������������r���������������ҵľ��顣����������������¼����
��������ʷ������Ʒλ�Ĺ���������Ȩ�ƵĽ���ʦ�����Ŷ��յĻʵۡ��Լ�Ϊ�Լ�Ӫ�죬������������������Ʒ��������¼����˽��ˡ����������������չ�ͳ���˼䣬�����밲�������������̾�̨�����ϵ���Ĺ���������DZڹ�·��Appian
Way���ϵĹŻ���ģ�°ͱ��׳ǵĹ��Ǹ�̨���Թŵ�����������Ĺ־���Ͼ��ǿն��ġ����١�����ͷ�Ρ���š��������������������������м��Щȱ���������Ĺ������壬�����˰��ŵ��¾ɳ����ֿ��Ĺ��ţ�������Ӣ�������ո����߽�ij��ǣ��Լ����к��ذ����俪��������ʽ��ϣ�������С�����������������֮��������������������С������壬�Է�֮�ĺ�����ж�µ����¹ں����籧����ֻ�������������30������Ǹ������������������˵��������Լ�����ϣ�����˼���������밮����ҹȺ�ǰ�������켣�������游����֮����ɬ��������
�����������������ֹ�������С��������ġ������۹�˥��ʷ������ܽ���λ�����۹�����������ʱ��ִ������������20��ִ����������12�궼���������㼣�鲼�۹�������ʡ������ǰ�����룬���ǵ��ں��ذ���С���ݼ���ϣ�����е�Ӣ�۰�����˹��Achilles����
������Ҫ����ȴ�����غͷ������ң����ߺ϶�Ϊһ��Բ�������ԡ�����֮Ѱ���������ǰ뵺���������������Ǵ�Į��������Ƕ����ӳ���ʢ�������İ��������ŵ��Թ���Ĵ��С��ٵ���觺��ϴ�ѩ���ǵ�ƽԭ��ÿһ�������������У�����������ͬ�ľ������ξ���������������������һ������ϣ�����������ζ�ĵ���������»ƽ����µ��ọ́�������������С��ķ�����
�����Ծ������δٽ�����֮����������������ۼ���ռ��������Ȫ���࣬ܿܿ�������ڳ��ڡ����������룬���ѡ��˱������ɡ��Ҹ���������������������Ǯ�ң�������壨Sparte���ˡ����䡢���塢������֮�����������ݡ�����������ǽ����ֺķ����������б���ҵ������������ʵ���������������硯��ָ�տɴ�����Ҳ�����˵���������Ǹ�����ū�ֶ��õı���������λ2000��ǰ�������ʵ����������̫ƽ�����ҿ����������Ƚ��շϳ���ū���Ƶĵ۹�������֮�ձ�������ȱ�����⡣��������ʶ��������֮����������Բ����������������Բ��ط��Ա��ŵڣ�ֻ��ϧȴ���������Լ���ʵ��������
��������һ���������������갮�˰���ŵ��˹(Antinous Mondragone)�ڹ�Ԫ130�����ˮ����Ϊ�硣֮ǰ�����ǰ��ú�ƽ���Ƴ����Ե�������֮��ȴ�����䣬��ΪѪ����ѹ60����̫�˵ı�������Է�����ʷҲ�Դ�Ϊ�磺�����۲Ŵ��Ե������ң����ֻ�����ڼ����л꣬����������ʯ����ÿһ�����á��������ò��������Ǯ�ң��������Ϊ��ۡ�������ڵ۹������е����룬��Ϊ���������Ͻ�����У����˼��ݣ�ȴ���ֲ����˵���֮ʹ��������֪�����Լ����������֮�£���ȴ�������Ρ�
����֮�糡����һ����ˮ���ڣ����ĵ���ֻʣ������������������ˮ�ɵ�Ӱ���β��ȱ��ƾ�����ڴ˱��Ŷ������������ӵĵ����������ʯ�������ŷ�ദ���з��鲼ŷ��С����ݡ�Canopus��ͷ���˵������17�������ھ��һ��������װ�������������������ٸԲ���ݡ�Canopus�ı̲���Ȼ�������ˣ�ƫ���������ܲ�����������֮�������ֻʣ��������ȱ������ʯ�����ۺ����˵ľ�ͷ�������Ǹ���λһ��������������������ʵۿ�һ����Ц������ݾ��ڽ��ԣ��ռ���ЩԷ�����������ʲ���ϡ������ש��������������������IJַ���Ϊ��Ӧ�������Ϸ��Ľ�֮������������Ϊ���������Сɽ�£�����¥��ƽ̨������¥���ڡ���ϧ�չ�ʱ��ίʵ̫�磬ֻ��������¥�����ڲ����������դ֮������͵����һ����ͷ�ޱ۵İ���ʯ��ȱ���������壬�İ����������ʯ��������ͬ�ձ���������������ϸ�壬��������������������ҡ�����������Գ�Цһ��Ϊ�˰���ʧ�ķ�Ļʵۣ�Ȼ��˭��Ȩ����Ц���İ��飿
������Է��֮�У��ڹ����������˺�����֮�䣬���ۻ������������������������ܵ�������������Ĺ��ͺ����ˣ����������ˣ�ǿ�������˺���ũ��18���͵�����ũ������ɽ�ȶ��ӣ���ũ�ᡢ�ַ���ţ���ˮ������Ƕ��������Χǽ��ص�����ս�����ɪ�ɶ�����ʱ�������ڳ����Ͽ��������˵�«έ����ȡů��ʣ�µ�¯��������������ů�����DZ���С˵��������ɩ����ʵ۵ĵ�һ�˳ƴ��ǣ�����Ӯ��ʷ�ϵ�һλ������ŮԺʿͷ�Ρ�
����������֧������������������ᵽ��������Ҫ�������Ĺ������������Ȼ�����ӡ�ʫ�ˡ����ˣ�Ȼ������Ҫ��������Ȼ�ǻʵۡ�����������û��ά�������ƽ�����µ۹����ã������˵��ҺͲ��ң��Ͳ��������������Ȥ����������ˣ�����26��϶������ļ���д���ÿÿ�к����ٶȶ��ʵģ����ǰ���ŵ��˹�����ա�����ʧ�ķ�Ļʵ����ͣ��������Ф���컹�Ƕ�ò�ʤö�١�����ʲô�ǹ��������Ų���������ʧ�Ұ�����ʹ��ĵ��������ϱڲ�ԫ�ġ�������С����ɺԵġ������ͼ����δ���ġ�����̫ƽ������Ҳ�ɾ���2000��IJ��ࡣ
ĺɫ�ĺ��У��߹����д�������Խ��������Ŵ�����ԡ�ҵ��ż�����ʯ�߰����ࡣ�����ǰ�����Բ����ž�����ף�������Բ�Σ����Ʒ���������������������ƫ������������Բ���У�һ�ܷɻ�����β���ӹ���ǡ������Ұ�д��¶�����б������Ƭ���乭����Ҳ������һ�̵Ĺ���ֻ�������Һ�ȴ�ޱ��������·���ʧ�˽������Щ����ޣ���������𣬿־��븧ο��ׯ�ϵģ������ģ����صģ��ḡ�ģ����ٵģ����ģ��ഺ�ģ�˥�ϵģ�����ģ����ģ�������һ��֮�ڣ����˻�Ȼ���ᣬ����ҹ����ˮ��
��������̣�֮ǰ��������ͣ��������ܹ�İ��������ȴ������ʯ֮�����Ϸ��������������δ������
�������ʵ۹�����(Publius Aelius Traianus Hadrianus,76��138)
���ŵ�����
�����������������빬λ�����������ĵ��������ǹ�Ԫ2����ʱ�������۹��ʵ۹������������һ��Խ�Ĺŵ佨��Ⱥ�����á�������С�����ʽ�滮���裬�ۺ������˹Ű�����ϣ�������������Ų��е����Ԫ�ء�
��ѡ��:��һ�����ں��˹Ŵ����к�����������������߱��֡� ���빬�ż����о����죬�����ո��˺Ͱ����ʱ�ڵĽ���ʦ�������ŵ佨��Ԫ�ص��ٷ����з�������Ҫ���ã�Ҳ��̵�Ӱ����20���͵Ľ�����ơ�
������ʿ
�������빬��Villa Adriana (Tivoli)
����ʱ�䣺9�㵽����ǰ1����Сʱ��1��1�գ�5��1�գ�12��25�ձ���
��Ʊ�� �6.5ŷԪ������ѧ��֤��ۡ�
�ִ�а�ʿ�����������͵�����֮�䣬���������ڳ˵���B�ߵ�Ponte Mammolo���������ڼ��ǹ�������վ��������Tivoli�� ��ɫ��ʿ��Ʊ��Ϊ1.6ŷԪ����ʱ40�������ң�ÿ15���ӷ�һ�ࡣ�ڹ������빬վ�³����貽��Լ800���ɵ�����������İ����Լ7�㡣
����Tiburtina��վҲ�п����������Ļ��г̴�Լ30���ӡ�
�ܱߣ�������С���ϻ���ͬ�������Ļ��Ų��İ�˹�ر��� ��Villa d��Es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