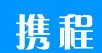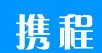| 策划、执行:Jane
摄影:沈煜
南非, 激情回响
世界杯时,你在南非嘛?我在。那些亲临的南非时刻,好似一块彩虹色的磁铁。其实,除了足球,非洲大陆最南端的一切都令人悸动。比赛结束了,而你我的探索,才刚刚揭开序幕。乌乌祖拉,在南半球的云天中一直无尽回响。
梦想建筑的奇迹
1992年,32岁的香港海关公务员Danny在公海上执行任务,如常,依旧。
他没有想过会离开香港。也没有想过,今后的人生,日夜面对的将会是西南半球另一个遥远大洲两个交汇的汪洋。
“什么?Danny,你要移民去非洲?那里可都是狮子啊!”诚惶诚恐的香港仔们这般嚷嚷。
1997年前夕,港人们经历了一波骚动,不少中产举家前往澳洲、加拿大。1993年,Danny选择了“都是狮子”的非洲,南非共
和国。
“我们开普敦的天气,真是很不错。”在南非已经居住了17年的Danny,如今是个忙碌的生意人。他的发色在17年间有了明显的变化,但港式的英文口音依旧清晰,笑容与谈吐也依旧是香港式的收敛与礼貌。他的独生女儿从小在这里长大,已经在开普敦念完了大学医科,“这几天,她在津巴布韦参与野生动物的救治项目。不过,她更喜欢香港,香港什么都有,热闹时髦,年轻人!”
冰冷的大西洋与温暖的印度洋在此汇合,四季海风吹拂,开普敦的空气因此完全没有污浊的机会。晴朗的日子,阳光如天梯一般,需要全天戴着墨镜。就算天气阴沉,巧云翻滚的天空依旧开阔高远。
如果不是来到这里,亲眼看到云卷云舒,建筑、公路、汽车、植物、动物、人,出乎意外的文明还有悠然的宁静,你也许会问,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为何选择移民来南非?肤色黝黑的Danny笑容充满感染力,移民之前他就来过两次,有朋友在这里,他发现,哇,原来南非是这样的!于是就来了,就这么简单。
也许这里钻石遍地,也许这里彩虹漫天。“无论对谁来说,离开自己温暖舒适的家,前往一片新奇而美妙(也许在最初时远称不上美妙)的土地,结识那里的人民,熟悉那里的文化,都将是个艰巨的过程。这种过程也许可以算是我们人生中经历的最难以应付的困境。”南非作家Dee
Rissik在《南非文化震撼之旅》一书中这样开篇。对于好奇陌生的旅行者,独辟蹊径的移民,这种迷惑的状态,是一种文化的震撼,让南非,如磁铁般吸引着远方的人们。
“得再看一眼南非的晚霞。”临走前的那一天,我们的摄影师在从克鲁格国家公园返回约翰内斯堡的高速公路上,看着落日以一种令人来不及捉捕的速度沉入宽广的地平线,他始终不肯放下手中的相机。第一缕南非的朝霞出现在我们到达那日的飞机机舱里。那时,他也一样兴奋地端着相机,不肯放过这同样异乎寻常的绛红色。谁说全世界的日升日落都一样?
这里可是南非!神奇的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国度。
更何况,全世界的足球明星此刻都在这里,乌乌祖拉响彻云天。
文/Jane
摄影/沈煜、张路宁
两洋相汇开普敦
岁月在两大洋的潮汐与海风中无声流淌而去,开普敦(Cape Town)有一个全世界最著名的海角,还有一座桌山,有着绝不同于非洲大陆其他城市的优雅旖旎。她在这片大陆的顶端,面向浩瀚的汪洋──更深处已是南极大陆,背对广袤的非洲荒原,如钻石的棱角,如舞者的足尖。
开普敦是个花园城市,有山有海,特别是这里的空气,简直是太好了!”Danny驾驶簇新的7人座Toyota保姆车从开普敦机场直接开往桌山
(Table Mountain)。南半球的冬季正午,阳光直射,人人都只身着单衣,鼻尖还渗出微汗。
“听说南非治安有点问题,是不是这样?”北半球游客被铺天盖地的负面新闻搞得神经兮兮,下飞机第一个问题直接关乎小命以及随身细软。
“开普敦的治安很好,你们大可以放宽心。只要不去不该去的地方,一定是安全的。”我们呼出一口长气,开始关心起天与地。
“你们运气不赖,这个完美的天气,去桌山,‘桌布’是完全掀开了的。而且明天晚上开普敦还有场球赛。”
“桌布?”
“云咯。桌山地处两洋交汇的特殊地理位置,加上地中海气候环境,挟带着大量水汽的东南风被桌山拦住后迅速上升,在山顶冷空气的作用下,一下凝结,翻卷的云团好像灰白色丝绒桌布将桌山围成裙摆。有时云雾也会偶然散去,这样的日子一年中屈指可数,而且每次也就持续数个小时。桌山旁边还连绵着十二门徒峰(Twelve
Apostles),就好像是上帝带着他的门徒们来此用餐。”我们的运气的确不错。因为球赛,桌山没有著名旅游景点到底是看人还是看景的通常顾虑。海拔1086米的桌山山顶的确如桌面般平坦,这平坦恰如刀锋削过,将山峰拦腰斩断,全山均为沙岩叠片构成。普通游客可乘与瑞士铁力士山同一模样的圆形缆车上山,索道全长1220米,每车可乘65人,从山脚升到山顶,正好旋转一周,是360度全开放视野,几分钟后便抵达山顶。登山者,可以走山路,靠近峻崖边缘。
我的旅伴Ben曾经在爱丁堡的Arthur's Seat一呆就是一整天。他喜欢在陌生城市的山顶俯瞰,别的,什么都不干。当我们站在“桌面上”,他说,再也没有比在天气晴朗的桌山山顶发一整日的呆,更适合做南非游的开篇了。整个开普敦城市与港口风光尽收眼底,如若换一个角度,在城区,随便一抬头,也可以望见独一无二的桌山。
每一个来南非旅行的人,倘若第一站是开普敦,一定会有一些质疑,这里难道真是非洲?165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为了在非洲建立一个补给站,选择了南非开普敦省的桌湾(Table
Bay)作为据点,以服务往来于欧亚间的船只。从建城伊始,开普敦一直是葡萄牙人、荷兰人、法国人与英国人争相做主的“客栈”。这座南非白人心中的“母亲城”,历经荷、英、德、法等欧洲诸国的统治及殖民,城市的模样,与人们印象中的非洲荒原大异其趣。
上帝长方形的餐桌安放在东大西洋海湾,远处大西洋里的椭圆形小岛是罗本岛(RobbenIsland),“Robben”在荷兰语中是海豹的意思,那里曾经关押过曼德拉等反对种族隔离的著名政治犯。约有3000名政治犯曾经在罗本岛上度过漫漫牢狱生涯,直到1991年最后一个政治犯被释放。
稍稍向东,便是更有姿色的印度洋了。大西洋,即便在夏天,海水依然偏冷,蓝色也偏淡。我同意Ben,因这唯美海湾,可以在山顶做一日停留,即使什么都不做,只是享受开普敦的日光、空气、海风,也不会感到无味,时光已在无知无觉间溜走。
桌山虽然沙岩叠片构造,植被却十分茂密,种类繁多,岩石的缝隙里都长满了灌木,山上的鸟类也多得出奇,保护区内有2000多种濒临绝种的原生花卉、植物,约150种鸟类。还有豚鼠、岩兔、蜥蜴在岩石上、小道旁,不避游人。上帝的餐桌,也是动植物们清新洁净的家园。
不得不再次提到开普敦的空气,开普半岛自东南方经常会有强风吹至,而当地人都将这股强风称为“开普医生”(Cape
Doctor)。这股风形成于开普敦西面的南大西洋高压脊,开普医生将清新的空气带来,把空气中的污染物吹走。
如果是往常,你很难在桌山络绎的游客中分辨出他们分别来自什么国家。这个时间,却很容易。不时有身穿自己国家足球队服的球迷,脸上用油彩描着国旗,兴高采烈地经过。下一晚的比赛是阿根廷对德国,偶尔有阿根廷的球迷在山顶上遇见德国人,火药味尤为十足,会挑衅般地打个招呼。
“嗨,你们猜,会是几比几啊?”
“当然是3:1,阿根廷队赢。”
“我看,是2:0,德国胜利。”
“那,走着瞧吧。”
身旁还有穿着大红色球衣的西班牙队的球迷经过,“是谁都没关系,最后总会遇见西班牙队的,嗨,你支持谁?”
“我?这我得问问章鱼保罗。”
绿点体育场(Green Point Stadium),从桌山上也能清晰地看到它坐落于信号山(Signal
Hill)和大西洋之间。绿点球场是世界上唯一一座有玻璃顶棚的球场,在世界杯期间,球场可以容纳66000人。
黄昏时间回到市区,维多利亚艾尔法特海滨购物城(Victoria & Alfred Waterfront)里连Fan
zone的球票都卖光了。这个依水而建的购物中心里,多家高级酒店的雅致外墙与温暖灯光投影在水面上,Cape Grace Hotel、Table
Bay Hotel曾下榻过无数名人。海湾中,还停靠着白天逡巡在大西洋上的游轮。
“今天晚上,章子怡已经到了。”Danny告诉我们。
“世界杯让南非热闹非凡吧?”
“是啊,你看看这些球迷。”
我们在Waterfront随便挑了一个西餐馆子,身边坐满了扯着大旗等着8点半球赛的球迷。当晚的这一场是乌拉圭对加纳。黑人服务员们在餐馆里忙碌穿梭。Danny推荐我们在开普敦吃海鲜。生蚝、虾、鱼都十分新鲜,做法也简单,我们要求一并烤了。在这里,尝尝鸵鸟肉也不赖。没过多久,样式齐全的海鲜烤盘已经送了上来,每一个服务员走起路来都十分抖擞,时不时来询问味道如何,也不忘瞅一眼墙上的电视机。
加纳队获得点球,射失点球。一分钟后,乌拉圭获得点球,进球,不算,再次射失。这戏剧性的一幕只在短短的五分钟内完成。双方球迷从狂喜、紧张、扼腕、失望,到再次紧张、惊喜、扼腕、失望。这就是足球,每个人都没有合上嘴,绿点球场、Fan
zone、Waterfront里的饭馆,全世界,人人都经历了相同的心理过程。
气氛真是好极了!身为连越位都不甚明白的女“球迷”,亲身参与了这惊心动魄的五分钟,深受气氛感染,已经在心里琢磨起来,下一次世界杯期间要在哪里旅行?巴西?!
欧洲后花园
开普敦的白人区以以爱德华式与维多利亚式的房舍最多。桌湾附近错落保存着18世纪的荷兰式建筑。去豪特湾(Hout
Bay)的路上,会驱车经过坎普斯湾(Camps Bay),开普敦的豪宅在此云集是有道理的──这里有迷人的沿海公路,十二门徒峰为背景,迷人的白沙滩,天体浴场,澄蓝的大海……典型荷兰式的房子,以清一色的芦苇为顶,散落在海边或者山旁,如一场童话。
这一路,不断有豪华跑车驶过,真是拍汽车风光片的绝好地点。除了跑车,还有哈雷摩托呼啸而过。Danny说,有一年,某一个医疗组织来开普敦开会,组织者临时通知各位与会者:乘坐的大巴坏了。不过,为了到达目的地,组织方为每个人准备了一辆哈雷摩托,请各位撅起臀部,坐上哈雷,尽快赶到目的地。
“山上的豪宅,有些自家造有缆车,方便上下,你们看看这些轨道。这房子,跟我们香港那些山上的豪宅一样。”Danny想必会问每个人可有兴趣来开普敦置业,想必每个人也都会盘算一下,要不下半辈子也如Danny一样,移民来开普敦?
从豪特湾坐船, 可以去往海豹岛( Seal Island)。这个季节,还不适合观鲸,但海豹却是没什么架子。岛上黑压压的趴着上百只海豹,为了海豹的生存,豪特湾海域禁止捕鱼。
在南非,放火抢劫也许不会坐牢,不过,要是你随便捕了一只未成年龙虾,就麻烦大了。在这里,破坏生态是重罪。
难道,南非?
在天上地上辗转了24小时,到家打开电视,重播着的比赛是阿根廷对德国。
记忆,找准一些节点,得以让时光倒流,真是一个很伟大的功能。
我记得我的那一刻,是在开普敦的Boulders Beach。快步跑去街道边的小商店里看一眼赛况。
“怎么样?”
“3:0了,阿根廷要输了。”
那个3 : 0 的时间点, 我们正在Boulders Beach,这里有成群的南非企鹅。
当然,这个时间点,天际线是白色的,那是渐渐黯去的天光。大海与天空,在白色的天际线处缝合,晕染。还有远处繁星般的灯火,安静得如停滞了一般的暮色,温婉的南风,从容的海浪,排着队,一摇一摆归家的企鹅。
傻愣愣的南非企鹅们,真的会排成一队,整整齐齐,慢吞吞地在海边的岩石上走。走得很缓慢,走得很拖拉。如果队伍中有一只停下来了,其余的,也都停了下来。无论如何,队形总是要保持的,这大概是企鹅的世界观。
到了4:0的节点,我们已经目送完企鹅宝宝们回家了,同时发现还有一条静直的街道,通往海边的停车场。四下,是开普敦的民宅,一栋栋房子,分插在街道两边。
比赛结束哨声吹响时,我们正“笃笃笃”地踏在静直的小路上, 街道、房子、海风、暮色、早起的星辰,还有气氛的祥和。我正努力分辨,这里是静谧的欧洲小镇还是澎湃的非洲大陆。
“是非洲。因为散着步的我们,身边竟然还跟着一只掉队的,傻愣愣的南非企鹅。”Ben一转头,无比不可思议地对我说。好望角,记得许下愿望标志牌上的经纬度这样标明:34°21′25”S,18°28′26”E。Cape
of Good Hope——美好希望的海角。
前几天,我收到Danny发来邮件,他说,你在好望角许过愿望,一旦梦想成真,要记得来回来还愿。这句话,上个月我采访过的歌手李健也曾说过,好望角,非常灵验,去的时候,记得许下愿望。
南非,在非洲大陆的最南端,从欧洲、亚洲、美洲,甚至是北非,到达这里都需要漫长的旅程。从上海出发,转机香港,到达开普敦已是26小时后的次日。而1488年,葡萄牙人巴索洛缪.迪亚斯(Bartholomeu
Dias)从里斯本出发,沿着非洲西海岸线一路南下,经过了数月的航行,发现大海尽头已没有大陆的踪迹,才来到了“非洲大陆的最南端”,他给这个岬角取名“风暴角”。
10年之后,又一个葡萄牙人瓦斯科·达·伽马(GamaVasco,da)再次来到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通过这里抵达了印度的西海岸。达·伽马自印度满载而归,葡萄牙国王若奥二世自此将“风暴角”改名为“好望角”——绕过这个海角就能带来好运。
在我8岁,也许,更小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地理老师——父亲指着地图上一个遥远的角落对我说,“好望角,世界上最险要的航道,惊涛骇浪,在南非的最南端。苏伊士运河没开通前,那些大大小小航船都必须经过这里,能不能顺利到达,要看运气……”
“如果有一天,我可以到好望角......”8岁的我,一定那样想过。
“好望角其实并不是非洲大陆的真正的最南端, 非洲的最南端应该是厄加勒斯角。”Danny在南非17年里,只陪同科考队的人员去过两三次厄加勒斯角,这个默默无闻的海角与好望角仅相距147公里,但远没有好望角耀目。大西洋与印度洋的真正分界线和交汇处在厄加勒斯角与好望角之间的海域内不断移动,随着洋流的强度、温差变化和月球的引力大小而不停地变动着。
Danny说,厄加勒斯角并没有好望角风恶浪急,岬角赫然。好望角,自从被葡萄牙人迪亚斯发现,在几百年间被人们赋予了无数的意义。传奇,总是被一再渲染,被人们各自想象,只能亲临,才能演绎出自己的一个版本。几百年前的欧洲航海者们沿着海岸线一路向南,当发现不再有陆地,当发现这也许已经是非洲大陆的尽头,会是怎样的心情?
Danny站在Cape Point遥指着大海,印度洋身后是亚洲,大西洋深处是南美,而眼前的海域,无尽的远方,是南极大陆。
不知道多少人在开普点(Cape Point)眺望两洋相会,会觉得这一切,非同一般。大西洋和印度洋在这里交汇,水下暗礁错综密布,水流莫测无踪,加上离南极较近,受极地气候的影响,这里终年大风大浪。好望角曾被来往的船只视为“死亡之角”。在开普点两侧的大洋,水温相差10℃左右,温暖的莫桑比克厄加勒斯洋流和寒冷的本格拉洋流在此汇合,在天气晴朗的时候,站在开普点上,甚至能分辨出两大洋颜色的深浅,印度洋深,大西洋浅。
互联网上,有这样的航海日记:“乌云密蔽,连绵不断,很少见到蓝天和星月,终日西风劲吹,一个个涡旋状云系向东飞驰,海面上奔腾咆哮的巨浪不时与船舷碰撞,发出的阵阵吼声,震撼着每个海员的心灵……”
在开普点不远处的洋面上,有一个白点,好像停在海上的帆船,又好像是跃出海面的鲸鱼,实则是耸起的礁石,而这片海域下,暗藏着无数的礁石,没有船只敢靠近这个海角。
一座1857年建造的古老灯塔默默耸立于开普点。100多年来,正是它为来往的船只导航。后来人们发现这座灯塔建得太高,容易被云雾遮挡,便弃而不用,又在开普点下方重新修建了一座新的灯塔。开普点的观景台上还设立了指向全世界各大城市的路牌。从南非的好望角前往新加坡9667公里,新德里9296公里,里约热内卢6055公里,耶路撒冷7458公里……
摄影师用上了Sony相机的最新技术,转动上身,用镜头连扫好望角与东方的印度洋面,生成宽幅照片。海与海角,天空,白色巨浪,飞鸟,连风的速度都可以在宽幅照片中捕捉到。
“航海者们千辛万苦经历了好望角的惊涛骇浪,进入平缓的流域,却发现,这眼前的一切,平淡无奇。还是一样的海面,还是一样的无边。而只要往前,再往前,就豁然开朗。远方是如蓝宝石般的印度洋洋面以及通往神秘富蔗东方的航道。”Ben望着一望无际的海与我分享他的发现。就好像是人生。经历了骇浪,未必立即绚烂晴朗。但只要再往前,再往前一点,也许就是天堂了。
离开好望角,已是黄昏。整个好望角笼罩在暖黄的光线中,我依然回望,白色的海浪打在黄色礁石上,千年万年,不曾改变。这个宁静的海角,寄托着无数人的向往,而我,自8岁起就惦记,终于来到。
文/Jane
摄影/沈煜
花园大道, 连绵怒放
从莫塞尔港(Mussel Bay)到斯托姆河(Storms River)绵延255公里的一级海滨公路,被称为花园大道(The
Garden Route)。每年1月下旬至5月,花园大道两旁会开满鲜花。据说这里集中了南非数千种花卉, 雏菊、普洛蒂亚、爱莉卡、百合、鸢尾花和兰花,争奇斗艳,花香袭人。其中普洛蒂亚是南非最具盛名的花种,在南非有超过350种以上的普洛蒂亚花。
名副其实的花园大道与海滩、湖泊、原始森林、肥沃山谷平行。南非的公路分三级:N(National) ,
R (Regional)以及M(Metropolitan)。我们沿着N级公路自开普敦开出,开普敦的黑人区在高速公路的两边,连绵数公里,只是普通游人,无从获悉里面的状况。南非的高速公路状况极好,河流自横卧东西的奥特尼夸山脉、齐齐卡马山脉流入蔚蓝的大海。一路驱车前行,山谷铺满了因地中海气候在冬季依旧幽绿的芳草,舒缓静谧的河流潺潺在山涧流过,还有迷人的海岸线,海风将海浪声拨入耳膜。
越过山脉,就是奥茨胡恩平原,从途中的关口要道眺望连绵群山,景色无与伦比。车行至Mussel Bay一定要去品尝一下当地有名的青口和生蚝。Mussel就是青口的意思。生蚝一打只要120兰特,我们阔气地点上一打来吃。这里的生蚝因为鲜美而泛出丝丝甜味。侍者说,今天买生蚝的,都有香槟送。气泡一下肚,立即脸红了起来,南非出产的新世界葡萄酒在全球充满竞争力。Danny带我们去山腰吹风,这种安排,极为适合陶醉了的人们。
当夜,宿在Mussel Bay的海边,酒店的窗户到海,只有十余米的距离。黄昏时刻,站在阳台上,可以看见有人在海中冲浪,那是印度洋的海水,冬日里依旧温暖。海岸边有零乱的石头堆砌,印度洋的海风丝毫不凛冽。有孩子在高高地荡秋千,与这活泼对比的,是山上无声的灯塔。
我选择在这里观星。海风将空气吹得清透,南半球的南十字星就在头顶闪烁,极容易分辨。几百年前,迪亚斯船队向北折回时,驶入一个植被丰富的海湾,土著黑人们在这里放牧,这个海湾正是莫塞尔港。这里有太多航海者往来的痕迹,荷兰水手写了信,就放在海边挂在树上靴子里,隔年另一位航行到这里的船员发现了这封信。老树邮局是南非的第一个邮局,著名的邮政树下的邮筒至今依然在用。
“见到远处山坡上的房子了没有?”Danny指着克尼斯纳(Knysna)的环礁湖边坐落着的芦苇顶的房子说:“这些房子,没水没电,但都是白人住在里面。去年,我和太太去采访过里面的人,没有水,也没有电,为什么要住在这里?”
“想必是因为清静。”我猜想。而我在香港机场买到的时尚杂志上吴彦祖的一篇专访也许已经给了我答案,“我和Lisa第一次去往南非,住在没水没电的房子里,面向大海。
我第一次与这个女孩儿,离开城市,纯粹地呆在一起,毫无干扰,也毫无消遣。这极度挑战两个人的关系,但是,我们觉得很舒服,无法离开对方。于是,我们选择了去南非结婚,就在这样没有电,也没有水的村子里,举行我们的婚礼。”
文/Jane
摄影/沈煜
克鲁格, 追逐“ 五大兽
南非,连钱币上印的都是野生动物。去到克鲁格国家公园前,我曾看过南非摄影家杰米·汤姆的一幅作品“初月映豹”。一只花豹栖息于岩石上,头顶是蓝色苍穹中的一轮满月,身后是南非丛林的斑驳树影。这幅作品,叫人忍不住惊呼,这就是自然之美!动物的表现力如此强大,让一切想象徒劳。
南非人Kevin有一双蓝色的眸子。这双眼睛,专注清澈。清晨5点,他驾驶着Safari专用的户外越野车来接我们。这将是一个动物日。这个点儿,天还暗着呢,Kevin提醒我们多穿点,敞篷越野开起来,风可是很大的。
克鲁格国家公园(Kruger National Park)是南非最大的野生动物园, 位于德兰士瓦省东北部,毗邻津巴布韦、莫桑比克边
境。公园占地约两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以色列的国土面积。非洲象、狮子、犀牛、花豹、猎豹、牛羚、黑斑羚、长颈鹿、斑马藏身于低矮灌木或高大的猴面包树间。野水牛、鳄鱼、河马在河流中度过每一个几近相同的晨昏。
克鲁格的每一个游客休息区(rest camps)都有一块黑板,上面标注着五大野生动物(Big Five)的踪迹。昨天、今天,在国家公园内的什么地点,见到过狮子、大象、犀牛、花豹、野水牛,就用相应颜色的图标标出。看起来,昨天的那群人,运气都不差。
这个国家公园内,狮子有1600多只,大象8000多头,一个水牛群有时超过500头。这么多野生动物!我坐在Kevin身后,看着他神采飞扬地开着车,心想着,等一下探索频道中那些花豹追逐牛羚、大象成群过河、动物们在草原上飞奔的情景总算都能见到了吧?
不过,当Kevin迷人的蓝眼睛不停地寻找,根据路上动物的粪便痕迹,小心翼翼地分析狮子是否有可能藏匿于道路两边茂密的丛林中,我就知道了要在克鲁格见到Big
Five并不是简单的事。公园地势辽阔,道路良好,每天早晨都有无数的车辆行进其中,然而,这里依旧是动物们掌控的天下。Kevin每天都在公园里转悠,对地形了如指掌,即便如此,神出鬼没的花豹依旧没能让人摸准它出没的规律。
“见到花豹,需要点运气。”Kevin屏息看着远处的长颈鹿。
“你们看这两头长颈鹿,它们不停地在警惕地回头,十点钟方向也许有凶猛的动物。”“有些时候,见到什么都需要点运气。”
克鲁格国家公园里遍地都是野生动物,这种美梦在中午过后已经在我脑海里破灭了。一整个上午,唯一见到的一整群动物是羚羊,间或有一群狒狒过马路,或者是优雅的长颈鹿站在远处的草丛里,探出它们的脑袋。在这和以色列一样大的野生动物保护区里,动物们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轻易能被游人发现。
Kevin始终专注研究着地上的痕迹。“也许有狮子在附近睡觉,看,这是狮子的脚印。”有时候,他需要拧开越野车的音响,放出狮吼的录音以吸引懒惰的狮子直起腰来。不过,大多时候,吸引来的,并不是狮子,而是兴奋的,无辜的另一车游客。“嗨,听到了吗?狮子叫。也许就在附近啊。”不时地把头探出他们的车,四下张望。
“也许狮子早就知道了你们的伎俩,才不会出来捕个猎给你们看呢。”
正说着,Kevin立即关掉了喇叭,“听到没,是大象的叫声,还不止一只。”
“你确定,不是别的车在放录音?”
“是真的大象。”Kevin很兴奋,调转头车,顺着声音而去。“也许,大象等下会走到路上来。它们的奔跑时速是40公里,跑起来飞快!”
随着声音越来越近,车上的我们也越来越兴奋,也许是一个象群在树丛后。象的吼声高亢洪亮,好似可以见到它们正扇着大大的耳朵,从丛林深处缓缓走来。然而,声音由远及近,又由近至远,等候多时的我们始终未能见到大象露出身影,直至那声音终于消失在了丛林深处。
Kevin举着望远镜,有些一筹莫展的样子。
Big Five一上午就没出现过。这是一场可遇不可求的完美邂逅。
“终于看到狮子了!”Kevin的对讲机里,有人呼叫。是两只,睡在离路边才20米的地方。Kevin调转车头,带我们去看狮子。果真,大大小小的车辆已经一字排开,各色长焦镜头驾起。森林之王,悠闲地睡在路边,连眼皮都不抬一下。不远处,还有一只白犀牛在踱步。Safari终于在午间十分达到了一个小高潮。二十分钟过后,狮子依然在睡觉,唯一的变化,是它们各自翻了个身。而白犀牛,一直不停地在踱步。动物们从来不关心人类怎样,在这里,它们才是真正的主人。
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太太举着望远镜久久地坐在河边,她是那么的耐心。我一屁股坐到她身边,打算找找河里是否有河马。“见到鳄鱼了吗?”
她凑过身子问,顺便把望远镜给了我,往三点钟方向指去。“看见了。”果然有大大的鳄鱼趴在河岸上,时不时眦开牙齿,面露凶相。不远处,还有河马一家,两大一小,悠闲地卧在水里。小河马十分憨厚活泼,在水里扑腾来扑腾去,一派祥和。可是我,依然还是惦记着Big
Five。
“有没有人被动物吃了?”我坐在车里问Kevin。
“每年都有。这里有些从津巴布韦偷渡来南非的人,经过克鲁格时,不幸成了动物的午餐。还有的是动物学家,去年,就有一个因为见到大象太过兴奋,一靠近就被大象踩死了。”话音刚落,我们又听到熟悉的大象叫声,可是,这一次,越来越近。
丛林深处, 这时走来了一大一小的两只象,这巨大的生灵,迈着优雅的步子,不徐不疾地,旁若无人地从我们车边走过。这个出人意料的情景,真是叫人惊呆,这画面的从容,叫人从心底生出无数感动。这就是神奇的自然,动物有动物们的世界,人类有人类的居所。应该相安无事地相处,应该彼此尊重。
目送着一大一小两只象的背影消失于树丛深处,我想起了一个公益广告。画面上,也是一大一小两只象的背影:
“妈妈,我长牙了。”
“……”
“妈妈,我长牙了耶!”
“……”
“妈妈!我长牙了!”
“……”
“妈妈……”
“妈妈,你不为我高兴吗?”
文/Jane
摄影/沈煜
钻石原乡, 黄金之地
还记得Danny提过的坎普斯湾(Camps Bay)的豪宅吗?那里有很多房子属于戴比尔斯(De Beers)家族,全世界几乎无人不知的“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的南非DeBeers是全球最大的钻石矿企业。而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钻石也出自南非的比勒陀利亚。这颗巨钻,被称为“非洲之星”,重达530克拉,有74个刻面,后来被镶在英王的权杖上。
像我这般,慕名而来的疯狂女游客,在南非,太容易因这些透明小石头激动了。“克拉”,对于全世界的姑娘们来说,都是一个多么令人齿颊留香的词儿啊!
世界上接近1/3的黄金出自南非。也就是说,这是一块黄金遍地的土地。
黄金矿城(Gold Reef City)在约翰内斯堡南部,矿井曾挖到地下3200米深处,现在这里已经变成了主题乐园。不过,我们依旧可以戴着安全帽,举着矿灯,乘搭内里的升降机,到地下220米以下的矿洞参观当时开采黄金的实际作业状况。乐园里,还生动地表演着黄金的实际融解和浇铸金币的过程。
黄金矿城如今已经是废弃的金矿,不过,1 8世纪后期到1 9世纪初期淘金热潮时期遗留下来的建筑和蒸汽火车,让我们轻易地想象着这片曾经挥汗如雨的黄金之地。
不过在今天,这里更是孩子们的天下。乐园门口,坐着一个彩绘师,一个腼腆的孩子正坐在她眼前,轻侧过身子,让她在脸上画上一个足球。
想起来了,西班牙与荷兰的对决,就在今夜!
南非旅行贴士
申请旅游签证要求:
1、填写并签名的申请表(可从以上网址下载)
2、有效期超过访问后30天以上的护照, 及护照首页复印件(A4)纸
3、照片一张(2寸彩照)
4、机票订单
5、酒店预订证明 (酒店直接确认,并用酒店抬头纸)
6、提供在南非期间可支付费用的财力证明(国际信用卡复印件,三个月银行对账单)
7、申请人单位出具的保证函(无业或退休者无须提供)
8、不可返还的申请费人民币560元整
9、可返还的遣返押金人民币15000元整
到达:
南非有九个主要机场,其中约翰内斯堡、开普敦和德班为国际机场。上海、北京每日均有航班直飞或经香港、新加坡等地转机至南非。
推荐航空公司:南非航空、阿联酋航空、新加坡航空、卡塔尔航空、国泰航空
货币:
南非的货币是南非兰特(Rand),它的国际标志是ZAR。1兰特约合 0.9131 人民币(以当日实际汇率为准)。在南非使用双币信用卡非常便捷。
时差:
北京时间减6小时。
气候:
属于温带地中海气候,四季凉爽,日照充足,全年均适合旅游。中国的秋冬季正好是南非的春夏季。夏季最高气温32~38°C,建议使用遮阳帽或防晒霜。
穿衣指南:
泳衣、防晒霜、遮阳帽、墨镜、舒适的鞋子、长袖衣裤都必不可少,夏天带单衣即可。特别注意,到野生动物保护区游览,应穿中性颜色的衣服,如棕色、米色和土黄色,白色和其他鲜艳的颜色会令动物不安;应穿长袖衣裤,以防被丛林中的蚊虫叮咬,传染疟疾。
购物:
南非的传统工艺品很有纪念价值,如碗、泥罐、珠饰、木雕、挂毯(动物毛皮)等,鸵鸟蛋绘画和木雕是最有南非特色的旅游纪念品。如果在南非购买的物品(食品等其它物品不能退税)价值超过250兰特,在离境时,可在机场办理14%退税(增值税)。退税时,请持有效护照,必要的表格及发票。
小费:
和欧洲一样,接受服务后应酌量给予小费,一般而言是消费价格的10%。
特别提醒
安全:
南非的治安状况总体上并不像媒体渲染的那么惊心动魄,对于旅行者而言,做到“三不要”:不要脱队单独行动;不要到黑人区;不要晚间外出,则在南非旅行和其他目的地一样安全。建议为个人、行李以及摄影器材购买保险。
生态保护:
南非的自然环境保护非常好,鸟类及各种小动物都不怕人,但不能随意捕捉或惊扰。此外,捡拾鸟蛋、捕捉龙虾、鲍鱼等都要申请许可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