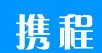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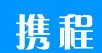 |
 |
 |
 |
文|蛐蛐 当苏黎世遇见尤利西斯 他在这儿活过,他在这儿爱过,他在这儿笑过,然后,他在这儿离开。每天,约有6万多人起降苏黎世国际机场,有300余辆列车进入中央火车站,有近40万个身影穿梭于利马河畔,他们在苏黎世出没,理由可能成千上万;但假如你在,我的理由便只有一个。 若我也可以扛一支8.75mm的电影胶片机,或许会从中央火车站门口阿尔弗雷德·俄谢(Alfred Escher)的背影切入,绕过蛛网般的电车线,顺着他眼神的方向沿班霍夫大街(Bahnhofstrasse)推进,随水鸟一起掠过苏黎世湖面,飞舞着,旋转着,俯拍着,直抵林登霍夫山丘(Lindenhof)上古罗马的断墙。 当镜头有意无意晃过一对相视傻笑的人儿,圣彼得大教堂(St. Peterskirche)正好敲响了欢快的钟声——那是一场婚礼的序曲,还是天堂又多了个天使? 光影中,渐渐清晰起来的,是灌木深处一方小小的石碑,上面刻着:“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1882年2月2日生于都柏林,1941年1月13日卒于苏黎世。” 时髦街区,寻不回旧时“希望” “这座城市简直太干净了,假如一盘通心粉被打翻在班霍夫大街上,你甚至用不着一把匙勺,就能立刻捡起来吃。”
与达达主义无关 只有大学街(Universitatsstrass)38号依然记忆清晰。当年詹姆斯·乔伊斯一家的新住处,现在立着关于《尤利西斯》的纪念碑,怀念作家如何在这套小房子里写出了一部旷世意识流巨作的开头。而后,乔伊斯一家又换到了街道对面的29号,乔家的女儿卢西娅(Lucia Joyce),也从一个任性的小丫头,长成了一位漂亮的妙龄少女。 今天,大学街29号成了一间可以帮人美黑肌肤的日光SPA店和一家二手书局。在密密麻麻的旧书架上,《尤利西斯》是其中的一本;紧挨着它的,是卡罗尔·L·席鲁斯(CarolL. Shloss)的《在清醒中舞蹈》,封面上的卢西娅·乔伊斯装扮成热带土著少女的模样,跳着印度尼西亚某种传统仪式舞蹈,美得仿佛祭神的精灵。 当时,一个叫“达达”的青年文学团体刚在苏黎世的伏尔泰酒店里悄悄形成,名字取自他们在法文词典中信手拈来的一个单词“dada”,意思是:无所谓、虚无、空灵,同时它也象征了婴儿牙牙学语时发出的简单音节,号称作家的创作应像纯洁的婴儿那样,排除外界其他干扰,只表现感知到的存在。 虽然热爱《尤利西斯》的人们一直在揣测:乔伊斯是否受到了达达主义的影响?但事实上,他更多出入的是来密大街(R.mistrasse)上的“官方大厅餐馆”,以及美术馆内的“孔雀餐厅”(Pfauen);偶尔,他也会去去美丽街上那家名叫“Odeon”的咖啡馆,或者“朱丽的老酒吧”(Jury's Antique Bar),一家整个从都柏林搬到苏黎世的爱尔兰酒馆。现在,酒馆的周围是苏黎世著名的金融区,出入的不是银行家便是证券商,人们或许没有时间了解那么多的历史和渊源,于是它的名字也直接改成了“詹姆斯·乔伊斯”,在一次重修中,巨型沙发的颜色统统换成了爱尔兰特有的浆草绿。 写作之余,乔伊斯喜欢步行到邻近苏黎世湖畔的耐德多夫大街(Niederdorfstrasse)上的中心图书馆借书。那里现在是整个欧洲研究詹姆斯·乔伊斯的最大的图书馆,至今还找得到他曾借阅过的大量希腊书籍,有的书页字行上用铅笔细细划出了杠。可以请求工作人员帮着复印他的笔迹,在复印中心的旁边,寂静地保留着作家的手杖、旅行箱、书籍以及死前拓下的面具。 这样闲云野鹤般地生活,直到他和家人搬去巴黎。
荣耀的作家,失落的父亲 20世纪30年代,乔伊斯重回苏黎世时,已是功成名就,著作等身的人了,他和家人住进中央火车站附近昂贵的酒店,对蜂拥而来的媒体说,没有哪里比得上苏黎世的医学技术和条件,而自己要回这里治疗眼疾。事实上,他有更加急需苏黎世的难言之隐。 这个可以用笔和英文记录世界的天才,却在管理财务和家庭生活上一塌糊涂,酒精害了他,而所谓的才气,在真实的人生里显得那么一无是处:在巴黎,他总是忙于自己的写作和出版,无暇关注子女的成长,而身为“名人”或“艺术家”的孩子,又是顶顶敏感和危险的。多情多艺的卢西娅,恋上了父亲的年轻助手塞缪尔,也就是后来写出《等待戈多》的男子,可他多次婉拒了她,令她几近癫狂,切断了父亲的电话线,在父亲的生日会上将椅子掷向母亲…… 那还是爸爸心疼的婴儿卢西娅吗?他曾为了哄她入睡,为她温柔写诗:“以前有个美丽的小丫头,名叫卢西娅,她整天睡觉,整夜睡觉,因为她不会走路,不会走路,她整天睡觉,整夜睡觉。” 那还是爸爸溺爱的小姑娘卢西娅吗:“在甘露和柔光中,月亮编一张网,宁静的花园里,一个孩童采撷单纯的生菜叶子。露水点缀她下垂的发丝,月光吻她年轻的额头。她唱一支曲儿:像浪花一样美好,你真美好!我祈愿,我的耳朵被蜡封闭,以免听她稚嫩的唱吟;我祈愿,我的心披盔带甲,把她护庇,采撷月亮的单纯孩童。” 现在的苏黎世联邦科技大学,全世界有名的“诺贝尔奖得主出产地”,有过伦琴、爱因斯坦、理查德·昆的地方,他带她去,并非要去拜访诺奖获得者,而是求治于一位著名的瑞士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弟子——卡尔·荣格(Carl Jung),分析后的结论是:你把自己的写作与女儿置于同等地位,不同的是,你沉醉其中,而她却溺水了。 几年后,当乔伊斯准备离开纳粹占领下的巴黎,全家搬回到苏黎世时,卢西娅却再也回不来了,她的国际旅行证件过期,被不停地转院,与家人永远地天各一方。 苏黎世动物园的旁边,听得到狮吼声的地方,长眠着詹姆斯·乔伊斯,他的身边睡着太太诺拉,那个曾答应与他一起来这个城市安家的姑娘;旁边还有没让他少操心的儿子,以及他的儿媳。至于卢西娅,如果你去往英格兰的北安普敦,记得替老乔伊斯在她的墓前放一朵花,让人心疼的姑娘,她的爸爸一直在等她回家。 苏黎世旅行贴士 当地交通:在苏黎世出租车的起步价是6瑞士法郎,之后每公里计价3.2瑞士法郎。苏黎世出租车服务公司免费电话:1551188。或者也可以选择在苏黎世火车总站18号站台免费借用自行车,带上护照和20元瑞士法郎押金即可。 节日及庆典:苏黎世节假日除了瑞士的全民假日外,还有贝西托而得日(1月2日)、六鸣节(4月的第三个星期一)、少年射击节(9月的第二个周末及接下来的星期一)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