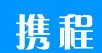|
土耳其,俗世的欢乐
位于欧亚大陆的交接点,土耳其是缔造过无限辉煌的国度,亚历山大大帝、恺撒、丝绸之路的商人和匈奴骑兵都曾在此跋山涉水,数不尽的遗址、废墟、王朝和文化遗产。从伟大的首都伊斯坦布尔出发,沿着古代商队的路线前进,穿过安纳托利亚中部,融入当地人的茶余饭后,去寻找仙人烟囱里的穴居者和消失了的奥斯曼时代。
伊斯坦布尔,帝国遗产
一道海峡横跨欧亚,它与两千六百年来的云起云落为伴;看尽良辰干戈,世上再没有一座城比伊斯坦布尔活得更明白。
“Merhaba!”你好,我现在正穿过土耳其第一大城市的街头,通过摄影机送上问候。
日光西落,月渐东升,六塔清真寺穹顶上鸥鸟盘旋,嚷嚷着不愿归巢。博斯普鲁斯海峡帆影浮动,两岸渐渐起了灯火,这一边是巴尔干半岛,那一边是小亚细亚,一水之隔,美得像部长篇史诗。
来自世界各地的纪录片工作者围拢在加拉太塔尖(Gelata Kulesi),聚焦2011年夏夜降临时的伊斯坦布尔,由IBM特邀拍摄,影像将在纽约林肯中心展映并永久珍藏;时间如水,人若行云,这个城市是浮出海面的真正主角。
一座充满秘密的智慧之城
伊斯坦布尔一看就是那种身世复杂的地儿。
首先,它姓名多变:拜占庭(Byzantium)、奥古斯塔.安东尼纳(Augusta Antonina)、新罗马、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每一次名字的更替,都伴随着荣耀、觊觎、信仰、征战、沦陷和重生。
其次,它地形曲折:房屋沿山而建,层层叠叠,密如鱼鳞,街道上上下下,时而逼仄狭窄,如入绝境,时而豁然开朗,大路通天;天连着海,海连着岛,岛连着渡轮,渡轮连着欧亚,起因可能只是搞错了一个门牌号,结果便横穿了两个大洲。
再者,它血统混杂:匈奴人、塞尔柱人、奥斯曼人、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希腊人、切尔卡西亚人(Circassian)、亚叙人、鞑靼人、波斯尼亚人、阿尔巴尼亚人、阿拉伯人、罗马人、犹太人……比如我有个朋友穆萨贝,他隆鼻深目,满头鬈发,张口却是地道的天津话,家里人竟从中国移过来,细说其详,便是一部漫长的迁徙史。
还有,它城府莫测:一座又一座清真寺,一座又一座公共浴室、一座又一座巴扎、一座又一座教堂、一座又一座皇宫,它们随山丘起伏,藏在苍柏、梧桐彼此意味深长的影子中。
这不,我正坐在色凯齐(Sirkeci)一带的站头上望眼欲穿地等公车,旁边人拼命挤眉仰脖努嘴让我看背后——一幢赭红色老房子,淹没在千千万万幢糅杂了巴洛克和伊斯兰风格的旧建筑中,铭牌赫然:东方快车(Orient
Express)。嚯,我的天!
过去,神秘的快车从这里缓缓开出,像铁轨上的宫殿,越过博斯普鲁斯海峡,一路开往遥远的西欧,其间上演无数爱恨情仇;现在,这里是被称为“史上最伟大的马尔马拉项目”(Marmaray)的起点站,它的完工将彻底改善伊斯坦布尔日益拥挤的交通,然而,它似乎永远也完不了工:工人们刚一开挖,就在乌斯库达尔(üsküdar)的地下发现了个古老的码头和市集;刚一开挖,又在耶尼卡皮(Yenikap?)的地下发现了个公元4世纪的拜占庭港口。
这座城市,地上地下藏着秘密,任何一个讲出来,都可能撼天动地。
每天,都有像我这样的人从各地各国来,试图去了解自公元前657年由拜占庭时代开始的细枝末节。我们发现了古老的街道、宫殿、浴室、蓄水池、跑马场、手绘瓷砖、公共汲水处以及完善的排水系统,其中的很多仍在被使用;而更多的,还长眠在现代伊斯坦布尔的某个角落——难以置信,2,000年前他们已经智慧如此,而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混沌不已。
这个地球上曾经文明最发达的城市,在19世纪随着奥斯曼帝国病入膏肓日渐式微,黄金时代的荣耀却藏也藏不住,在一砖一石上熠熠发光。
圣索菲亚大教堂(Aya Sofya)皇室之门东南的侧廊上有一张哭泣的脸,脸上被刺穿了一个小洞,如果你将手指伸进去,拿出来要是变湿了,所有伤痛都将不治而愈;地下水宫(Basilica
Cistern)西南角幽暗的石柱下也有一张脸,它是长了蛇发的美杜莎,白鲤神不知鬼不觉地从旁边游过,水滴凉飕飕地滴落在颈部。
我走进托普卡帕的后宫(Harem),想象自己是被黑人宦官从人口市场上买来的外国丫头(因为伊斯兰教禁止奴役穆斯林),马上要接受长达7年的宗教、文化、语言、化妆、穿衣、家政、音乐、举止、舞蹈、绣花等教育,努力着想成为嫔妃身边的侍女、太后面前的红人、真正征服苏丹的人。
雕花大门在身后重重阖上,参加完割礼仪式的穆斯林男孩身着苏丹王袍,举着小权杖庄严走下石阶。谢天谢地,这只是一场戏,我们随时可以在苏莱曼大帝的禁城中游荡,也随时可以作别郁金香时代(Tulip
Era)所有的荣华、财富、权势和阴谋,奔向自由、喧闹、无束缚的烟火现世。
繁荣市井的延续
大巴扎(Grand
Bazaar)如迷宫般曲折,日日人声鼎沸,它仿佛是个带顶篷的城中之城,几个世纪以来都是伊斯坦布尔的市井中心。我的身边,是吆喝琉璃灯的、镶珠宝的、批发肚皮舞裙的、称金银首饰的、出售皮衣的、编制花边的、叫卖手绘瓷碗的、端茶送水的、打情骂俏的、顺手牵羊的、讨价还价的……
这里有超过4,000家店铺、数公里长的货物通道以及清真寺、餐馆、警察局、银行、作坊,甚至还有个东方的亭子(Oriental
Kiosk)和粉红色的大客栈(Zincirli Han),单从建筑的规模和装饰的精美,便能推测苏丹穆罕默德二世至苏莱曼大帝统治时期贸易该是何等繁荣的景象!
做买卖的良好守则从那时沿袭下来,无论是流动小贩还是富可敌国的巨商,大都不强买强卖;你若犹豫不决,问来问去,他们也不太会给脸色看,还可能请你喝上一杯土耳其茶。
姆里斯.甘巴提(Muhlis
Günbatt)端坐在他那间装饰华丽的铺子里,隔着落地橱窗看外边人来人往。他身形魁梧,眉宇威严,面前的苹果电脑不断闪烁,接受来自世界各地的订单,小到奥斯曼风格的手绣长袍,大到铺天盖地的基里姆(Kilim)地毯,件件价值不菲。
他推荐给我的每样东西,我都爱不释手,但当他说出价格后,我全大呼小叫着嫌贵。他一点也不恼,反而笑眯眯地请我坐下,一击掌,从后间唤出了两个漂亮姑娘,一个奉上洒了柠檬古龙水(Kolonya)的擦手巾,一个为他捏起了肩臂胳膊肘。
桃红、橘黄、翠绿、靛蓝、绛紫在布匹上肆意怒放,他呢,则气定神闲地为我一解释起那些精美的花纹、细致的针脚以及每一种色彩所代表的意义,比如紫色,那是属于奥斯曼王族的专用颜色,象征尊贵和不可侵犯。
不断有人进来看货,德国的、法国的、西班牙的、英国的,姆里斯敬而不媚地用各国语言照应,回头坐下,冲后间一击掌:“看茶。”
“你的架势好像苏丹。”我笑他。
他却一脸镇定:“嘘,告诉你个秘密,我其实就是苏丹……大巴扎里的。哦,对了,你从哪里来的?”
这个问题,我在伊斯坦布尔每天要回答起码几十遍。“你从哪里来?”,软糖店的小伙计问,香料市场批发茄子干的问,烤肉店的厨子问,茶馆里的老板问,面包铺的学徒问,旅馆的看门人问,铁作坊的大爷问,花市里的吉卜赛人问,推了一车香草的小贩问,拐角卖青李子和开心果的摊主问……起初我以为他们的确对答案感兴趣,并觉得这是对自己耐心的极大磨练;后来发现并不是这么一回事,他们其实把这句话当作打招呼、问好、搭讪、开玩笑、推销、解闷、表示友善的一种方式,你到底从哪里来,他们可能前问后忘记。
前世今生 不知疲倦
好朋友欧妮(Oney)打电话来让我过去做客。她在塔克西姆广场不远处有个老房子,过去是亚美尼亚富商的宅邸,后来因历史原因破败得不成样子,她花了相当于6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将它买下重新修复,现在市价已经翻了无数番。这笔买卖七八年前就听她提过,当时她建议我也考虑在伊斯坦布尔置点业,最好选在贝伊奥卢地区,也就是加拉太大桥北边的海岸线开始,包括塔克西姆广场和繁华的独立大街。
19世纪中期,这里住满西欧的外交官和商人,建筑完全是当时西方最流行的风格,充满着各种时髦玩意,不仅通了电灯电话,还有全世界第一条电车轨道,人们称此地为“小城中的欧洲区”(Pera)。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建立,那些人作鸟兽散,周遭一片衰败。
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贝伊奥卢重拾旧日辉煌,每天都有新潮餐厅或咖啡馆开张,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的高级夜总会是土耳其名流和明星出没的地方,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进的。望得见金角湾和马尔马拉海(Marmara
Denizi)的私家屋顶上躺着时髦男女,喝香槟,看日落,而我只能远远眼红着,为自己当初对伊斯坦布尔的无知悔恨不已。
我们在加拉太塔附近曲折的小巷穿行,那里隐藏着无数私人博物馆、服饰设计店和精品小酒店,艺术家们站在老公寓的阳台上抽烟,见卖贻贝的小贩或卖香烟的人经过,就垂下根系了里拉的绳下来,下面人心领神会,把要的东西系上去。
鱼市(Bal?k Pazar)里摆满黑海里刚运来的鱼鲜,“鲜花长廊”(Cicek Pasaji)里全是小餐馆,里面挤满下班后的雅皮,个个光鲜。老话说,如果你没去过最传统的小酒馆(Meyhane),简直愧对伊斯坦布尔的夜色,我们终于在阿斯马兰赛特(Asmalimescit)那里的REFIK找到了个位子,四周坐满喝茴香酒的人,侍者托着五花八门的小菜穿梭,任人挑选。
我们用比周围人更高的嗓门聊天,从著名品牌Yargici最新一季的橱窗布置、Inci鞋的式样、,聊到会让睫毛飞速长长的甜杏仁油;从中村的集市、守在海边等鱼吃的猫、排长队的巨型烤土豆(Kumpir),聊到法国学校(Galatasaray
Lycée)对面的THEHOUSE咖啡……
聊起土耳其男人,我说,他们真是爱搭讪,油嘴滑舌得可以。她不置可否:“那些是做买卖的,其实大多数土耳其人都很害羞,无论男女。”
她让我仔细听背景里若有若无的传统音乐,“是不是总觉得很忧伤?”当我回答“是”的时候,街道上却极不配合地传来简直要把屋顶掀翻的尖叫声—费内巴切队赢了全国足球联赛—这些疯狂的人!
因为喜欢伊斯坦布尔,有人进了苏丹艾哈迈德老城区,就再也没离开半步;因为喜欢伊斯坦布尔,有人在集市区逛了几天几夜,还恋恋不舍。当年十字军东征从海上过来,望见它的高大城墙和金色塔尖,顿时被如此辉煌惊呆;我从它的前生醒来,又在它的今世沦陷,不知疲倦。
安纳托利亚中部,遍地传奇
从托钵僧的故乡到凯末尔革命的出发地,从塞尔柱商队的驿站到奥斯曼时代的小镇,历史俯拾皆是。在这片广袤的平原上,恺撒大帝喊出了传世磅礴名句:我来!我见!我征服!
听说我要启程去孔亚(Konya),几乎所有人都莫名其妙:“你大老远地跑去那里做什么?”
一来因为孔亚在普通土耳其人的眼中非常“保守、宗教味儿十足”,二来因为每年一度的梅乌拉那节(Mevlana
Festival)是在12月,只有在那时候才能欣赏到真正壮观的、与信仰神秘结合的、灵魂出窍般的托钵僧旋转舞(Sema),平常日子都不过是给游客看的表演而已,还不如就近去伊斯坦布尔的征服者清真寺(Fatih),那里是仅存不多的托钵僧寄宿地,有原汁原味的仪式。
我起先犹豫不决,但好朋友欧妮的电话坚定了我出发的决心。
孔亚 带着缺陷来,完美无瑕地离去
欧妮告诉我,她的家祖籍就在孔亚的伊来里,是4000年前赫梯人(Hittites)的后代。这些日子,妹妹菲雅(Feryal
Oney)正在孔亚举办个人巡演,将融合了土耳其多民族音乐元素的新民谣作为送给故乡的礼物,她是著名的Kardes Türküler乐团主唱,每周电视里都能看到她主持的音乐节目。
孔亚立刻变得亲切无比。从机场驱车前往孔亚老城,一路上蓝天白云、广阔的牧场,看起来那么令人心怡,远远地,一座铺满青灰瓷瓦、有着凹槽穹形屋顶的奇特建筑出现在视野里—梅乌拉那纪念馆。
公元13世纪是属于孔亚的,也是属于梅乌拉那的,他原名鲁米(Rumi),是土耳其史上最伟大的诗人、数学家和哲学家,传说当年他在孔亚讲经,听者无不动容。
穿过放满石棺的小院和清洗喷泉,脱鞋进入诵经室,在陵墓入口处,沉重的奥斯曼木门上雕刻着这样的字句:带着缺陷来,完美无瑕地离去。
每年有超过200万的穆斯林来此朝圣,他们伏在梅乌拉那的陵墓前低声祈祷,相信他能听到并给予神般赐福。
“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国际化的土耳其人,你如何看待他?听说阿塔图克.凯末尔并不喜欢他。”我扭头轻声问朋友。
“对我来说,某种意义上他更像是位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好比你们的孔子。梅乌拉那的苏非派(穆斯林神秘主义教派)倡导保守的处世方式,所以奥斯曼帝国的历代苏丹出于统治目的都是它的信徒;但凯末尔建立共和国后下令禁止,因为认为它是土耳其推行现代文明的绊脚石。现在,它作为人类的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被重新理解和保护起来。”
也许我该冬天再来,看身体如何旋舞着成为星座,看灵魂如何从日常琐碎中神奇地飞离,而不是买门票参加一场应景的表演;现在,不如去到城那头的阿拉丁山(Alaaddin
Tepesi),山上有一座几个世纪以来不断被毁坏、重修、装饰又毁坏的清真寺,如今东边的入口处看起来像个敲破了的蛋壳。
而我们真正想做的,就是躺在清真寺后面那片青草坡上,加入当地人的野餐,和他们一起“咔咔咔”地嗑瓜子儿,闲谈吹牛,变成像他们那样爱讲笑话的及时享乐者。
古丝绸之路
离开孔亚时,我们沿着古代的丝绸之路前行,大草原平坦无际,只有永远想去远方的风滚草才会偶尔做做同道。
大约一个多小时后,我望见了整个安纳托利亚地区最大的苏丹大客栈(Sultanhani)!它有着炫目的雕花大门和巨大的露天庭院,中央是凸起的祈祷室,四周环绕着寝室、饭厅和厨房,鸽子成了这里的主人,它们在马厩拱廊上筑巢,无辜地瞪着门口的不速之客。
13世纪时,塞尔柱王朝为了鼓励贸易,为骆驼商队一路修建了许多供休息的驿站(Caravanserais),按一天可能的行程设置,每站之间大约相隔15到30公里,修建、维护以及商队住宿的费用统统由苏丹承担,而他则从贸易的税收中得益。
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则热心于在城镇中心修建小客栈(han),还提供就餐和办公场所,这样更便于商人们每天来往于集市和休息地,接近于我们现代的中央商务酒店。正午的安纳托利亚中部炎热干燥,日头明晃晃地晒着,假如你是一位牵着骆驼挥汗跋涉的商人,这时候除了客栈,最想看到的是什么?对了,当然是水源。
真是想什么得什么。远处的天际线下正横贯着一条粉蓝的光带,漫长、美轮美奂,我们再三确认那不是海市蜃楼而是土耳其第二大内陆湖后,全都欢叫着冲它飞奔过去。不晓得这算万幸还是不幸:湖边白花花的结晶盐扎得脚底生疼,湖水咸得让人差点变成蝙蝠——原来,土耳其80%的食用盐全来自这个湖,所以它有个听了就立刻觉得口渴难忍的名字:咸水湖。它的形成,是由于古时候的海底经地质变化隆起,受到雨雪和常年累月的风蚀冲刷,岩层中的盐分日渐析出使然。湖边的男孩们捧着一罐罐浴盐作去角质霜,见人就抹;他们力荐的浴盐SPA,不但能美体,还提供无限清凉畅饮,每个人都被说得心里痒痒;而对于丝绸之路上的骆驼商队来说,走到这里,我猜或许改做盐商更能看到前进的动力。
番红花城 遇见甜蜜的意外
与跋山涉水,以物易物相比,能在番红花城拥有一间小铺子简直是天堂般的生活:
冬天在那里做点生意,卖香料也好,卖蜂蜜也好,卖土耳其比萨饼(Pide)也好,卖水果干也好,夏天就搬到郊外的葡萄园里避暑,用藤上的绿色嫩叶包裹着香喷喷的米饭和开胃菜蒸熟,淋上新鲜酱汁调味,就着红石榴汁(nar
suyu)或者清爽提神的土耳其酸奶(ayran)—神仙来换也不干。
伊斯麦.乌卢卡亚(Ismail Ulukaya)老汉就在三座山谷交汇处的老市场里有间小杂货店,但他同时还有另外一个身份:番红花城的钟楼守护人。
每个星期一和星期四,当宣礼塔远远传来第一声召唤,他就洗漱干净走出家门,沿着山坡步行20分钟,然后攀上山巅高耸的钟楼,在仅够转身的狭小空间里,仔细检查和观察钟表运转情况,一星期用巨大的工具为它上一次弦。直到日薄西山,宣礼塔里又一次传来召唤,他才下塔,锁好门,一路闻着花香或是迎着纷飞的雪花回城,顺便到土耳其浴室(Cinci)洗个热桑拿。
这样的日子,他坚持了46年,当初从生意的合伙人那里学来这门手艺,一直从小伙子干到两鬓斑白,不计分文报酬,只觉得骄傲。
“这个大钟,是1797年由当权的大维齐尔从英国进口来的,安装在番红花城是因为它是奥斯曼帝国通向黑海的贸易要镇,金钱流进流出的地方,这样的报时钟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在土耳其都是非常少见的。”
乌卢卡亚老汉听着悦耳的齿轮声,像听见孩子的歌唱,当钟锤整点撞向大钟时,青山翠谷间都回荡着他的笑声。
因为还出产珍贵的药用番红花,整座小镇曾富可敌国,城中遍布漂亮的奥斯曼老宅,一般都有两三层,上面的楼层突出于下层,层与层之间用雕刻精美的粗木框架撑起,填充泥砖和麦秆,然后抹上灰泥。房主越有钱,就越会在木框架和墙面上做足装饰功夫,手绘上花鸟或者把木天花板雕成枝状吊灯的模样。
我们住下的那个宅子,就有10个左右的房间,分成男屋(selamlik)和女屋(haremlik),间间设计巧妙:被褥藏在干燥的浴室里、浴室藏在橱柜里、取暖系统藏在墙壁里、绕着墙壁的长榻拼起来就是床……
为了避免抛头露面,女子通过可旋转的橱柜伺候来访的男客,但有时她会把字条悄悄藏在茶碟下,转给墙那边心仪的人;等橱柜再转回来时,茶碟里也许多了一块软糖(lokum),上面撒着番红花粉—那是他从城中老店Safrantat为她带来的意外甜蜜。
“老城的模样看起来和我小时候没多大变化,可是孩子们变自由了,”乌卢卡亚老汉感叹道,“这是好事也是坏事,不再有人对看守钟楼感兴趣,他们也许更喜欢去安卡拉见世面。”
安卡拉 一个世俗共和国的首都
我们到安卡拉并不是为了见世面,但在安纳托利亚的广阔乡间和小镇住了这么久,重返大都会,无论视觉还是听觉其实都受到巨大的冲击。
所以当我在安卡拉的火车总站(Gar)外出现,看见匆匆忙忙赶路的人流和车流;或者在卡瓦库来代大街上出没,与长腿蜂腰的美女、面目俊朗的型男擦肩,觉得自己就像个大开了眼界的乡下妞儿。
阿塔图克.凯末尔深爱这座城市。在他来此之前,安卡拉还被叫做“安哥拉”(Angora),历史上它是个是非之地,无数征战和掳掠,后来穷得只剩下安哥拉山羊和安哥拉兔了。凯末尔把这里当做革命的策源地,1923年独立战争胜利后,他宣布它为土耳其的新首都,并给了它崭新的名字。
伊斯坦布尔人或许嘲笑这里是“英雄的人民,光(是)灰的城市”,但凯末尔爱它。
他有8年时间从未去往伊斯坦布尔,一心要把安卡拉变成真正的大都会:他为它修了宽阔的林荫大道,将沼泽地改造成了有湖水的森林,把穹顶的老集市重修成了博物馆(Museum
of Anatolian Civilisations),重新规划了街区住宅,人们都有了属于自己的姓氏……
眼神深邃的凯末尔婚姻并不如意,也没有一子一女,全土耳其的人都是他的孩子,他们为他建起宫殿般的陵墓,至今仍称他为“父”(阿塔图克),因为他为他们建立了一个真正的世俗共和国,并带领这个国家在高度现代化的欧洲立得一席之地。
我在他的墓前献花,以一个安纳托利亚的旅人之名,感谢他为这片土地缔造的传奇。
卡帕多细亚,穴居者的秘密
从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发,向东南车行两个多小时,一片月球般神奇的地貌开始出现:仙人烟囱岩里,可能藏着教堂、餐馆和客栈;白色悬崖边,也可能凿满蚂蚁洞般的地下城市—这里便是卡帕多细亚,不可思议的人类居住地。
假如你像我一样,乘热气球在清晨飘落于安纳托利亚高原,定会看到奇异的岩柱冲天而起,像一支支仙人烟囱(Peri Bacasi),而某些地方,又仿佛干涸的外星球被上帝摆满锥形小山丘,丝毫看不出任何人类出没的痕迹。
但随着晨曦迅速点亮峡谷、沟壑和山峦,投下神秘的影子,有人开始懒洋洋地从地下、从洞穴里钻出来,在葡萄架、橄榄林、橘园、菜地和新收获的麦田间留下行踪。
仙人烟囱岩 非人间的景象
卡帕多细亚地区有着无数远离尘世的小村落,它们被安顿在蜂窝状的白色悬崖下,几个世纪以来,村民们就生活在那一根根巨型蘑菇般的岩柱或者迷宫般的地下洞穴中,养鸽子、喂牲畜、种菜、生儿育女。
当18世纪的探险家保罗.卢卡斯(Paul
Lucas)回去向法国人描述这里的居民如何聚居在小金字塔样的圆锥山洞里时,人们都以为他在瞎编;1907年,另一个法国传教士从这里策马经过,立刻被双眼看到的一切惊呆:在清早灿烂的光线里,那些山丘和沙谷构成了非人间般的景象。
我和朋友赶在夏天的清早过来,在格雷梅那些悬崖峭壁上下攀爬,寻找拜占庭时期开凿出的教堂、卧室和餐厅,它们曾是早期基督徒的避难所,如今是土耳其最负盛名的世界级文化遗产。
数百万年前多次的火山喷发造就了卡帕多细亚独一无二的类月地貌,早期喷发出的物质形成了下层的松软的凝灰岩,之后发生的喷发则为其包裹上了一层坚硬的玄武岩。随着雨水、风以及沙的侵蚀,最终形成了现在这些巨大的山地、峡谷和蘑菇状的仙人烟囱岩。
几个世纪来,人们出于避乱、因地制宜、冬暖夏凉等目的,在山中开凿巨型堡垒,在地下挖掘建造了数百座深达数层的洞穴,地下地上连接在一起,构成了世界上最震撼人心的居住景观。
这些千奇百怪、高低不等的镂空石丘、石柱和石丛,环抱着古老的小村庄,我们沿寂静起伏的街道前行,时不时有小孩和包着头巾的女人躲在门缝后吃吃地笑,要是凑过去,她们便像受惊的猫儿一样逃掉;村中央是建在仙人烟囱岩和石窟中的罗马陵墓(Roma
Kales),几个男人正笨手笨脚地移栽一棵老桑树,他们说不远处的洞窟是全世界最大的不明飞行器博物馆(UFO
Museum),而山后的岩洞里,住着能与动物对话的马语者。
在卡帕多细亚,遇到什么样的奇人奇事我都不会觉得奇怪。
我们没找到那个传说中的神人,于是决定不如找家开在仙人烟囱岩里的洞穴餐厅,大吃一顿。
洞穴宽敞巨大,蜿蜒纵横,凉爽异常,丝毫没有想象中的压抑感;墙壁上绘着几个世纪前美丽的壁画。土耳其人喜欢吃烤肉,但在卡帕多细亚,有一种叫做Testi
Kebapi的特色当地菜,它是将涂了洋葱酱和蘑菇酱的肉串,放在一个密封的陶罐里慢慢烤熟,端上来时当着客人的面打破罐子取出烤串,香气满溢自然不在话下,关键总能引起一片欢呼。
侍者们送来了Turasan葡萄酒,装在仙人烟囱岩状的瓶里,卡帕多细亚充裕的光照和肥沃的火山土质孕育出了甜美多汁的葡萄,在那些陡峭的山谷中,散落着一些小葡萄酒酿造厂,它们还延续着奥斯曼帝国时期的传统工艺,酒体深邃,口感醇厚。
我用一份甜蜜的果仁千层蜜饼(baklava)作为这场洞穴大餐的尾声,它中间夹了蜂蜜和香脆的坚果;而我的朋友则尝试了貌似油炸糯米圆子的甜品,我们曾在土耳其的无数地方看到过这种东西,其实它是裹着糖浆的炸面球(Künefe),还顶着一朵冻奶油,空口吃简直甜得脑仁疼,只有配上土耳其茶慢慢食,才能心平气和体会它的口感。
谜一样的洞穴城
整整半个下午,我都在凯马克勒蚁穴般的地下城中钻来钻去,它向着地心深处挖掘了8层,藏着谜一样的隧道和洞窟,如果不是有指路标记,也许我至今还在里面钻来钻去。
那些被熏得漆黑的窟窿,以前是厨房;那些仿佛还能闻到草料和粪便味的空穴,以前是牛棚;那些带圆磨石的,是谷仓;那些有圣坛的,是礼拜堂;那些放石凳的,是学校……在公元6到7世纪时,假如波斯军队打算出兵,警报几个小时内就会从耶路撒冷传到君士坦丁堡,当信号传到卡帕多细亚时,这里的拜占庭基督徒们便携家带口,逃往通向地下城的秘密通道。
上下层之间以石梯连接,每一层入口都用一块可以滚动的巨石挡住,隔开各户之间的隐私,墙上凿有通话孔。深达100多米的通风井为地下送去空气,地面部分被聪明地伪装成水井的模样,即使波斯军队往“井”中投毒企图污染水源,也只是中计。
而这并非唯一一处地下城,在卡帕多细亚,迄今已经开放的就有36座,据推测还有上百座,城与城通过数十公里的地道连接,之间还有无数条小型隧道,简直难以置信!
当时约有3,000多人住在凯马克勒,往往一住就是数月,警报彻底解除后,这里变成储藏酒和食物的地方,因为它终年保持恒温。而我现在必须爬出地面,趁还没变成幽闭恐怖症之前,在杏树阴凉处好好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风从峡谷那边吹过来,鸽子站在悬崖边咕咕歌唱,戴菲斯毯帽(fes)的小贩把手工冰激凌搅得满天飞,它由山羊奶和研碎的野生兰花根茎做成,吃起来舌尖芬芳绽放。
一位穿免裆碎花裤裙的中年女人在不远处整理她的摊子,我一直想买些长长的花边可以挂在脖颈上,那是如今伊斯坦布尔派对上最时髦的式样,细长的丝线上缀满牵牛、铃兰或者可爱的小樱桃,可联排大巴扎(Arasta
Bazaar)里价格惊人,没想到这荒郊野外竟然有。
与一身穆斯林农村妇女的土气打扮相比,她的英语好得出人意料,原来曾远嫁澳洲,但与在西方文化下长大的土耳其丈夫性格不合,她选择回到自己的山村,在凯马克勒地下城附近开一个小商铺,发动周围村子里的妇女织毛衣、绣花、钩花边,她利用语言优势把传统的土耳其乡村手工艺品卖给外国游客,让毫无经济能力的妇女也可以补贴家用。
“为什么不是选择去伊斯坦布尔那样的大城市呢?单身一人不怕村子里的人嚼舌头吗?”我替她担心。
她耸耸肩:“的确会,但我不在乎。我想帮助家乡的姐妹,让她们知道自己的能力可以改变命运。”
田园牧歌的生活 热情的民族
卡帕多细亚当地人传说,要是你从内夫谢希尔(Nev?ehir)山上的古城堡眺望一眼,你定会情不自禁在此待上七年。
结果我望了一眼,当即被山谷中田园牧歌般的生活吸引而去:一位头巾大娘在桑树下卖坚果,她似乎更醉心于东瞧西看,自己嗑掉的瓜子比卖掉的还多;几个妇女坐在村头聊天,其中一位手里紧紧攥了只鸽子,我不晓得她到底想去送信,还是准备马上炖了它。
我正热火朝天地抡起锄头,帮一户年迈的婆媳除草,对面人家热情地隔着街招手邀请过去做客。
我从旅行指南书上学到,拜访传统的土耳其家庭,一般得带份小礼物以示礼貌,比如一盒果仁蜜饼或者土耳其软糖。可没有准备,我们啥也没带。但主人的热情很快消除了我们的尴尬,他们像招待久未见面的孙辈,恨不得把家里最好的东西都拿出来给我们看给我们尝。
在土耳其旅行,有一个细节让我深感温暖:他们总是像家人一样称呼陌生人,比如这家的老大爷,就慈祥地称呼我们为“我的孩子”,还忙不迭地吩咐他家大婶赶紧煮茶、准备银茶具、摆出椰枣、巧克力和各种果干,一个劲儿地让我们吃让我们喝。
土耳其人偏爱产自黑海地区的茶叶,最好用传统茶炉来煮,下面是巨大的装水的母壶,上头的子壶里装茶,母壶里的水沸了,冲入子壶,然后将子壶中的茶汤倒入小小的有托碟的玻璃杯里,配上一块方糖,全国上下老老少少都用它来消磨时光。
至于土耳其咖啡,它相当浓,喝完后杯底总留有一层厚厚的渣,这时将杯子倒扣在杯碟上,根据咖啡渣自然形成的图案和水流,预测爱情和凶吉,其实是不断制造聊天话题的好办法。
大爷大婶一句英文也不会说,而我们的土耳其语又极其有限,急得脑门冒汗怎么办?没关系,只要记住竖起大拇指,不断发自内心地夸赞:“巧客故赞!巧客故赞!”(非常好吃!非常好吃!)
我们在茶香和不舍的目光中告辞,暮色四合中,清真寺的穹顶美得像一幅剪影。村边的广场起了夜市,卖菜的父子忙着摆摊拉电灯;女人们终于结束了村口的闲言碎语,各自返回忙碌的厨房,男人们则聚在茶馆里抽水烟、喝茶、打几圈土耳其麻将,然后被一路小跑着来的孩子拖回家,定是已经预备好了香喷喷的平底锅煎肉、蛋奶面糊条或是土耳其牛肉饺子,再来一小杯茴香酒——小院里还绽放着粉色的玫瑰,屋顶上还晒着忘记收回的杏子干,知了唱着唱着就开始发梦。
假如我说,我开始考虑在土耳其买下一间屋,春天来便到迪来克(Dilek)看花,夏天来就徒步到凡湖找会游泳的猫,秋天来就随秃朱鹭一起从加济安泰普(Gaziantep)开始迁徙;若是冬天怎么办?冬天那就骑上一匹枣红烈马,走山关过雪原,从阿马斯拉一路去往锡诺普(Amasra
to Sinop)!
|